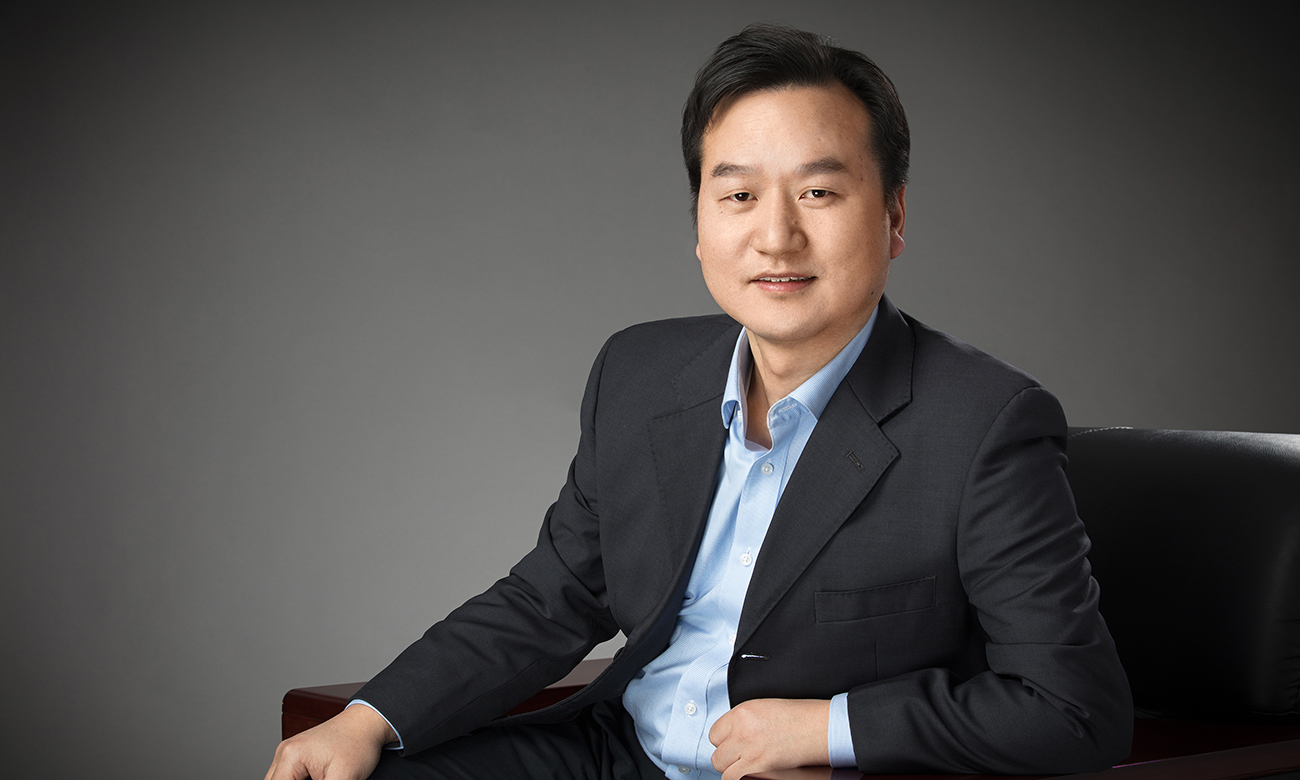
2005年,山西左權的一位農民,影響了劉冬文的職業軌跡。這位農民從劉冬文當時管理的中國扶貧基金會下的一個項目貸了500塊錢,一年期,前兩個月不還錢,后10個月每個月還50塊錢。
“我當時很好奇,問他貸500塊錢能做什么?”現為中和農信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劉冬文回憶道,“他說,可以買一些修縫紉機的工具,因為他在煤礦工作得了硅肺病,不能干重體力活,他就幫人修修縫紉機,還款的壓力也不是很大,所以他還非常自豪。這給了我很多感動和啟發。”
18年后的今天,劉冬文領導著中國規模最大、覆蓋范圍最廣的農村小額信貸平臺。他擔任董事長的中和農信是一家專注服務農村小微客戶的機構,在全國400多個縣設立了分支機構,員工人數超過6,000多人,貸款余額達150億元。
“貸款意味著機會,貸不到就沒有機會。那我能不能給窮人一個同樣的機會?”劉冬文近期在接受《財富》(中文版)專訪時說。這句話是貫穿他逾二十年職業生涯的一個持久信念。
2008年正式成立的中和農信,前身要追溯至1996年世界銀行在中國展開的一個小額信貸試點項目。2000年中國扶貧基金會接管這一項目,當時在國務院扶貧辦負責管理世行項目的劉冬文就此參與進來。他發現,國際上有很多類似項目最后都成功轉型成為商業化運作且可持續的機構,比如專為窮人服務的銀行,甚至還有上市的,但在中國還沒有出現成功的商業化試點。他大膽想:我們為什么不能去好好做一次呢?
2005年出任小額信貸部負責人之后,劉冬文開始往這方面去嘗試。他的思路很清晰:第一,只給窮人或者說中低收入農戶貸款,不跟銀行搶客戶;第二,不能躺在捐贈或政府補貼上,而是要實現商業和財務可持續。
到2008年時,這兩個目標都已實現,小額信貸項目的利息收入已經完全能覆蓋幾乎所有支出,從一個政府公益項目改制成商業實體的時機已成熟。這一年,這個項目從中國扶貧基金會獨立出來,中和農信正式成立。
此后的15年間,中和農信市場化進程中又邁出過關鍵的兩步:一是數字化轉型,二是引入影響力投資者——后者被劉冬文稱作“耐心資本”。技術與資本的雙重加持,使得中和農信在不需要財產抵押,也不需要政府擔保的情況下,無抵押貸款占比和整體還款率達到了99%以上。
在創業之初,劉冬文嘗試回答一個問題:窮人是否也講信用?用二十年的實踐,他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財富》(中文版):面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小額借貸,是一種普惠性金融。當初是什么促使您走上這條路的?
劉冬文:普惠金融的概念已經出現二三十年了。最早的普惠金融叫微型金融,其實就是給窮人貸款,比如諾貝爾獎得主尤努斯教授他們那批人,通過比較好的產品和服務設計,讓窮人也能以市場化的價格獲得貸款,并通過自身的發展去擺脫貧困。
我在國務院扶貧辦的時候對這個理念就非常認可。我自己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每年會回家看一看,發現我們村里的那些家庭,都是靠自己的勞動做個小買賣或出去打工賺錢才擺脫貧困的,而靠國家各種補貼的家庭其實都是擺脫不了貧困的。當你給這些想通過自身努力去改變現狀的一些人哪怕提供很小的支持,他們也會非常珍惜,他在發展過程之中如果賺錢能力得到提升,規模越來越大,可能就會達到銀行的門檻,未來從銀行獲得貸款。
實際上每年都有一些優質客戶從我們這里“畢業”,成為銀行的客戶,我們也是在為那些被傳統銀行排斥的人培養信用記錄以及提高他的還款能力。所以我經常跟同事說,你們不要擔心銀行來搶客戶,我們這個機構最大的愿望就是所有的客戶最后都能到銀行去貸款。
《財富》(中文版):中和農信的無抵押貸款占比和整體還款率達到了99%以上,這相當高了。你們在產品設計方面有哪些創新之處?
劉冬文:跟銀行比,我們一般更愿意給個人貸款,我們覺得法人貸款的問題在于所有法人都是有限責任,而個人的責任是無限連帶的,也不存在破產的情況。銀行更希望給法人貸款,可能是因為小微企業的法人貸款有一些政策的扶持。貸款額度上,我們也比銀行要小一些,貸款額度太大就超過了借款人的承受能力,過度負債可能給他帶來的不是正向激勵而是反向負擔了。
我們做了這么多年,目前筆均貸款在3萬-4萬,最高的額度也就是20萬,只有個別地方能到30萬,整體業務10萬以上額度的貸款占比只有4%。還有我們的還款方式也比較靈活,可以整貸零還,也可以整貸整還,可以先息后本,也可以先還百分之多少后還百分之多少,可以根據客戶的特點和需求來決定。
產品標準和服務流程方面有三點。第一是產品的門檻要低,因為如果門檻定得太高,就不能服務到真正需要這些貸款的人群;第二要充分發揮本地人的優勢,因為從純財務的角度,你可能沒法對一個客戶做出能不能貸款的評判,但是本地員工利用一些他在本地的人脈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可以很快做出一個貸款決策,這是很多所謂的互聯網金融解決不了的,也是我們獨特的優勢。
第三就是我們在設計產品和服務流程時始終堅持簡單化和標準化。比如我們現在到銀行做一筆貸款,可能要簽幾十頁的貸款合同,但我們就是一頁紙的合同,甚至連一頁紙的合同都沒有,就在手機上簽署。我們不像銀行,客戶經理可能要科班出身或有工作經驗。我們在當地招的員工可能只有初中以上的文化,如果我們的產品和流程是簡單化和標準化的,一個員工經過幾天培訓就可以開展業務,半年到一年后就可以成為一個合格的客戶經理。我們每個客戶經理都是要負責一個片區的,比如說負責一個鄉鎮,這個鄉鎮的所有村子他都要走家串戶去做營銷,如果有貸款需求他要上門調查,并上傳信息。然后當地要開貸審會,從放款到收款,包括貸后的回訪,都是信貸員要負責到底的。
《財富》(中文版):信貸員確實比較了解當地情況,但另一方面,會不會有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放貸權為自己謀取私利?你們如何規避這樣的道德風險?
劉冬文:首先我們的貸款利率比銀行要高一些,這是一個天然的排斥機制,能在銀行獲得貸款或社會融資能力比較強的人不會找我們來貸款。同時,如果他是一個有正常還款意愿的人,也不會利用關系去套取我們的貸款。只有那種不管利率多高、借錢就不打算還的人,可能是道德風險會出現的情況。對此我們也有一套完整的內控機制,比如做貸款審批時我們首先要做大數據的風控篩查,如果借款人的征信很差,我們就會立刻拒絕。第二我們要做交叉驗證,因為我們在分支機構除了有客戶經理,還有督導和主任等,我們有三個層級的人在當地工作,他們有交叉驗證,而且如果貸款額度超過5萬,還要經過貸審會的審批。另外我們要求貸款必須打到借款人本人的銀行賬戶,而且這個銀行賬戶是經過驗證的,所以通過一些技術控制以及人工控制的機制,我們可以很好地規避掉這些道德風險。

《財富》(中文版):2016年12月,螞蟻宣布戰略入股,成為中和農信的第二大股東。與螞蟻合作的契機是什么?近六年的合作過程中,中和農信的最大收獲是什么?
劉冬文:2016年時我們要做數字化轉型,數字化工具對于提高效率和降低道德風險非常有好處。恰好螞蟻當時來找我們談業務合作,讓我們推薦一些客戶給他們做助貸,雙方合作很愉快。當時我們正好也要引進戰投,另一方面也想借助螞蟻的數字化能力,一拍即合。
和螞蟻的合作,很好地解決了我們IT人才建設的問題,我們的CTO從2017年開始就是由螞蟻外派擔任,現在已經是第二任了。我們和螞蟻有約定,CTO必須由我來提名,提交董事會投票決定,這個制度是為了保持我們在IT系統建設方面的獨立性,畢竟我們的業務跟螞蟻的業務是在完全不同的層次和細分市場,而且螞蟻在董事會中也只代表一小部分。我們對CTO的考核也比較苛刻,達不到KPI的話可能會被退回去。
《財富》(中文版):既然中和農信已經是一家企業,盈利永遠是第一或者至少是重要目標。普惠性與盈利性之間必然會存在一定的沖突,如何平衡?
劉冬文:這兩者對我們來說是同等重要的。首先,我們堅持普惠,鎖定目標客戶群體不偏離,因為這部分客戶群體是一般商業機構不會去服務的,同時如果我們長期服務這個群體,就會比較了解這個市場,也就形成了我們的競爭優勢。而且這個事在中國更有意義,我們為銀行培養客戶,銀行會很開心,再加上支農支小也符合國家的大政方針。這些都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政治保障和社會氛圍。
但如果僅有普惠性,而企業是虧損的,那麻煩也會很大。這首先會導致員工的不穩定,甚至業務也沒法開展;第二會導致我們沒法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無論是債權投資人還是股權投資人,都要看到我們有合理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才會愿意投資給你或者把錢借給你。所以我們在堅持普惠性的前提下一直在提高效率、控制成本,確保投資收益達到合理的水平,讓投資人滿意和放心。
我們的股東一半以上都是“影響力投資者”,或者說看重ESG的投資人。我們的股東構成其實也經歷過幾個階段,一開始主要是政府支持,然后是扶貧基金會主管,基金會有足夠的耐心和試錯成本可以讓我們不斷地在小范圍小規模試點,之后我們才引進了國際金融中心(IFC)這樣的發展類機構,以及包括紅杉資本、TPG和螞蟻這樣既有情懷也愿意在這方面承擔更大風險的機構。這些機構都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讓我們可以不斷去探索,他們也愿意接受可能失敗的結果,當然最后我們并沒有讓他們失望,還是走出來了。但是如果前期沒有他們這樣的耐心資本,可能我們也走不到今天。
《財富》(中文版):你們接下來還會繼續引入這類投資人嗎?
劉冬文:如果條件合適,我們還是會愿意繼續引進一些戰略投資者。我們現在有150億左右的貸款余額,其實規模還是比較小的,覆蓋的縣只有400多個,而全國大概有2,800個縣級行政區域,其中僅農業縣就有近2,000個,也就是我們當前服務僅覆蓋了20%,實際上還有很大的市場空間可去拓展。
當然我們也可以去做債權融資,但是如果自有資金不夠的話,我們最終還是需要有股權投資進來,所以目前雖然我們沒有經營方面包括現金流的壓力,但從市場拓展的角度來說,如果有合適的資本,我們還是會愿意引進一些。
《財富》(中文版):融資難、融資貴是普惠金融一直遭遇的難題。中和農信在融資方面有何優劣勢?
劉冬文:如果說要跟持牌金融機構相比,我們肯定更難一些,因為他們可以有存款,這是最便宜的資金,同時他們還可以用央行的支農再貸款或扶貧再貸款,另外他們在銀行間市場融資也很便宜。而我們的錢主要來自于銀行,也就是銀行融到資后批發給我們,我們的成本肯定比銀行要高。
其次,如果是跟一些頭部的互聯網金融公司相比,由于它們母公司的背書能力比較強,很多金融機構也愿意給它們融資,包括給它們發ABS等,所以它們的資金成本比我們也要低一些。
但如果是跟其他小貸公司相比,我們的融資成本還是比較低的,因為畢竟我們的運作更規范。所以整體來說,我們的融資渠道是打開了,只是在成本上有一定的挑戰,而如果我們的融資成本太高,這個成本也會傳遞給客戶端。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兩難的處境。但只要我們持續規范開展業務,金融市場對我們還是會比較認可的,擴大規模可以進一步壓低融資成本。
《財富》(中文版):中和農信在全國400多個縣設立了分支機構,員工人數超過6,000多人,其中80%為縣域及鄉鎮員工,這類員工可能并不那么好管理。你們是如何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管理體系的?
劉冬文:通過二十多年的摸索,我們形成了一套適合農村小貸業務的管理架構和流程。首先,我們有總部和分支機構,類似于麥當勞開店,有技術含量的方面全部放到總部來設計和完成,而分支機構層面主要是銷售人員,他們去做推廣、放款和收款。也就是說,復雜的內容通過標準化的設計和培訓去傳導,或者做進系統里通過程序或機器去實現,這樣到了縣一級才能讓那些客戶經理即便沒有從業經驗也能干這個事,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優勢。
第二,我們形成了一套文化,就是讓這些員工不僅覺得這個工作我能干,還覺得干了這個工作有價值,很體面,因為收入也還不錯。我們設計了一些激勵機制,比如五險一金,因為在農村很少有公司愿意全額給他們繳納五險一金,而我們從成立到現在一直堅持這么做。同時我們也有一套辦法來評判一個員工是否合格或高效,因為銷售人員的收入跟業績是直接掛鉤的,如果他的收入老是在低水平徘徊,就說明他不適合干這個崗位。
另外公司也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幫助員工提高效率和能力,比如讓他們不僅可以做貸款,還可以去做保險的推薦,或者農機、飼料和化肥的推介銷售,相當于可以交叉營銷。這樣員工在下面跑一趟就會發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工作效率無形之中也就提高了很多,也多了一些其他的收入。當然我們也有很多的規則,比如內控機制,如果員工觸犯了紅線,就會受到嚴厲的處罰,包括開除或者扣除誠信基金等。通過這些,我們就能讓員工既能開心地干,也能規范地干。

《財富》(中文版):中和農信在中國是一個很獨特的存在,幾乎沒有跟你們直接可比的機構。村鎮銀行可能有一些相似性,但近些年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并未探索出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對此您怎么看?
劉冬文:出問題可能是因為國家的期望和村鎮銀行經營者的訴求不匹配。中國不缺銀行但缺為農民服務的銀行,所以當年推出村鎮銀行,是想模仿國外社區銀行這類機構,希望它們服務農村客戶,但是很多村鎮銀行的經營者可能并不是這個想法。比如,村鎮銀行要由商業銀行來發起,而商業銀行可能更多是把這當作開分支機構的機會,畢竟開設分支機構一般是需要審批的。也就是說,大家的初衷和訴求不一樣。再加上村鎮銀行很多都引進了本地化的一些企業,而企業可能也是良莠不齊。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在做中和農信的時候,強調首先要符合國家的大政方針,否則就會出問題;第二要符合我們自身的愿景和使命以及價值觀,否則凸顯不出我們的優勢;第三要真正滿足客戶的需求,這也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根本。(財富中文網)
編輯:王昉






